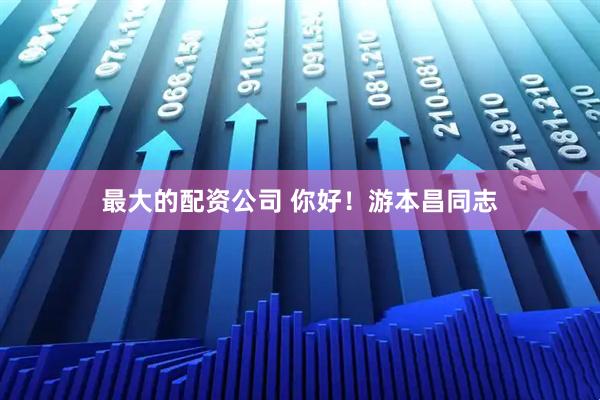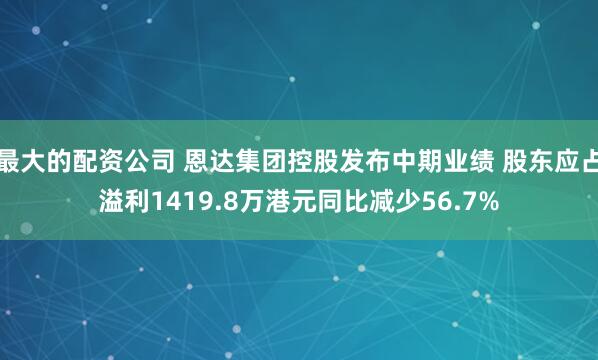剧版《繁花》中李李被带到派出所调查在线配资查询服务,同时接受调查的还有南国投上海总操盘手强慕杰。
事情的起因是南国投涉嫌二级市场违规收购上海瀛洲实业公司(剧中的601股票)。强总的收购虽然不合规,最多也就是罚款了事,李李将信息透露给宝总,宝总如果选择不跟,这笔大买卖就此擦肩而过,如果宝总在公示前重仓跟进,那就涉嫌“老鼠仓”,一旦坐实,宝总是要去踩缝纫机的,强慕杰出手的确够狠。
资本的残酷本就如此,现实中的发生的真实事件更是惊心动魄。
剧中的南国投说的就是深圳宝安集团,瀛洲实业则是上海证券市场最早的八家上市公司之一,民间称为老八股中的延中实业。
这是我国第一例资本收购战,被称为“新中国资本战争第一枪”,只是苦了那些炒家,一些加了杠杆的跟风者在“第一枪”声下几乎倾家荡产。
八十年代,延中工业公司只是上海静安区的一个街道企业,王牌产品是晒图机,一年的利润在百万以上,这在当时已经很牛了,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,急需大量资金。
幸运的是,延中赶上了好时代。1984年上海出台政策,鼓励新办集体企业发股融资。
当年,申请上市者和管理者都是摸河走路。由于政策规定只能是新办集体企业可以上市,延中注册了空壳公司,取名延中实业。
因为是新公司,工商注册和上市规章之间出现了相互矛盾的问题,经过工商局和金融处(当时审批上市发股的是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)协商后,延中工业公司拿出30万资金,注册成立延中实业公司,工商执照到手后,交给金融处审核发股,等到延中募集的资金到位再增加注册资本。

80年代的延中打印社
这样一来,延中实业要想成功上市,必须募集到足够的资金。
延中的管理者计划拿出70%的股份,向社会个人进行出售,股票的面值100元。
当年,很少有人知道股票这玩意,延中生怕自己股份卖不掉,经上级同意,搞了个有奖销售,奖品是一套二房一厅的新工房。
1985年1月13日,延中实业股票正式向市民认购。
这一天,成了上海滩的大新闻,前来认购的市民非常疯狂,交通严重堵塞,警察比市民更紧张,唯恐搞出不可收拾的局面。
说实说,绝大部分人都是冲着房子去,股票什么的少有人介意,只当是买几张彩票。
当时的销售现场实在太火爆,几乎难以收场,为了避免出现意外,领导们商量后决定增加供应量,从企业认购的份额中拿出总量的20%,总算是勉强收官。
最后的结果,延中实业的法人股(当时报表上的名字叫单位股)仅占10%,社会个人股占比高达90%、股权极为分散。换句话说,只要拿到11%股份,就能实际拥有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。
这为以后的“宝延风波”留下了隐患。
股份抢购的最大赢家,是上海毛巾厂的一位工人,他幸运地抽到了大奖,一套住宅。
1990年底,延中实业敲响了上市锣声,代号600601,简称601。但是,由于缺乏经验,公司章程中没有标注任何反收购的条款。
上海的股市,从1990年12月的100点开盘,一路涨到1992年5月的1429点,一年半涨了近15倍,巨大财富效应之下,上海人简直疯特了。
管理者为了解决交易柜面严重不足的问题,上交所在文化广场组织百家证券公司联合办公,首日开门营业竟来了4万余人,当时的场景吓死了在场的工作人员和领导,匆忙决定临时关闭。经过多次演练,调整,一个礼拜后才恢复运行。半年后,也就是1992年底,这个违规的临时场地终于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。
文化广场证券超市关张一个重要原因,股市开始退烧了,1993年证券市场迎来了第一次大熊市,一熊就熊了三年。
在一片绿色之中,延中实业的股价却出现明显异动,股价从最低的8.8元最高涨到44.20元,9月14日后,更是连涨11天,遥遥领先。
9月30日临近午间休盘时, 上海证交所突然宣布对延中实业实行紧急停牌。
随后,深圳深宝安集团发布公告:公司实际拥有延中实业普通股5%以上。
10月4日,宝安集团再次公告,持有延中实业股票15.89%,宝安事实上成了延中的最大股东。
事情被公开化,大股东延中工业公司才如梦初醒。
10月5日,上海延中首次公开回应宝安的收购行为,总经理秦国梁对宝安持有延中股票的合法性提出质疑,指责宝安在二级市场的收购属于违规操作,涉嫌恶意收购,要求监管介入调查。
同一天,宝安集团总经理陈政立紧急抵沪,据传陈总这次来上海的行踪非常隐秘,一个晚上连换了三个酒店。
那个年代的治安状况一言难尽,很多地区都发生过血腥事件,陈总生怕上海方面找他麻烦,背地搞一些栽赃陷害的动作,宝安集团异地作战,谨慎小心也是情有可原。
上海毕竟还是讲规矩的地方,地方行政部门并没有强力干涉,只作壁上观。事后来看,宝安集团的谨慎多少有点心虚和小气。
接着,延中实业开始反击,聘请施罗德集团和香港生源公司担任反收购顾问。
延中虽然是集体企业,毕竟也算国企,上海的政策又远不如深圳灵活,很多的做法,在深圳被默许,在上海则被严格约束。
反收购专家提出的包括“毒丸”在内的很多方案,都牵扯到延中的资产计损,在当时的上海,国营资产的名义损失,是一道红线。
延中实业曾经想过联合本地企业在二级市场进行反收购。由于,股价已经被炒上天,此时入场难免去替别人抬轿子,就算惨胜,宝安集团照样赚了个盆满钵满,延中则要承受股价回落后的巨大账面浮亏,而且,短时间内一时无法筹措到巨额资金。
这些努力,最后都只能作罢。
宝安集团在这次收购中,动用了6000万资金,在九十年代,这是一次巨大的赌博。
宝安集团也不是没有软肋,按照当时制度,收购达到5%必须公示举牌,之后,每增加2%都需要公示。
但是,这项制度存在一个漏洞,没有对 "一致行动" 人作出定义,宝安公司借助上海分公司和其他关联企业,化整为零,分头行动,以“一致行动人”来逃避限制规定。
上海延中在政策束缚之下,只有紧紧咬住宝安借助多个法人账户,联手违规购买股票问题不放,并且深挖对方举牌前后的大量“老鼠仓”,一并提交给证监会,要求监管介入。
《繁花》中的李李利用信息优势,每天5万股跟仓601,如果是在举牌公告前买入,就是明显的“老鼠仓”行为。

10月6日,宝安集团陈总亲自拜访延中实业,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和解,表示这次收购是善意的市场行为,并不想改变企业现状。
延中实业的态度则相当强硬,先搞清楚宝安的股东合法性,再做下一步讨论,会议不欢而散。
双方协商没有结果,延中还有最后的底气,吃准对方最担心、最害怕就是被拖入诉讼,不管胜负如何,一旦进入司法程序,很容易拖上个一年半载。宝安在二级市场呼风唤雨的6000万资金是有成本的,时间越长越拖不起,况且还牵涉到“老鼠仓”,如果查实,将涉及刑事犯罪,宝安的结局恐怕只剩下身败名裂。
10月中旬,延中实业正式向上海法院提起诉讼,控告宝安违规持有延中股票。与此同时,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和协调。
深圳宝安集团显然有备而来,动用上海的资源,并在背后很是做了一些工作。
最终,通过上海证管办协调,双方达成谅解,避免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。
1993年10月22日,证监会作出了最终处理决定:宝安公司立即停止收购行动,承认其所拥有延中19.8%股份的合法性;关联公司的24. 6万股延中股票利润归延中所有;对宝安公司的违规操作予以警告并处罚款100万元。
至此,深宝安与延中实业管理层达成合作协议,深圳宝安正式控股延中实业。
这场资本争斗,被称为“宝延风波”,是中国证券市场上首例公开收购上市公司的事件。
在这次风波中,宝安也做了一定的妥协,宝安派遣上海公司总经理出任延中实业董事长,但并不拥有投票权,原董事长周鑫荣保留其投票权,直到退休,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全部留任。
实事求是地说,“宝延风波”中深圳宝安的有些做法可以说是明目张胆的违规。
但是,同样不可否认,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,宝安打响的中国资本市场并购第一枪,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。
整个事件的主要策划者,宝安集团的陈政立和厉伟,不仅魄力大,更是精于算计。
选择熊市出手,监管的容忍度相对宽松,这是天时。

选择延中实业,也是经过慎重推敲,延中从里弄街道厂起家,政府几乎没有投入,就是静安区集管局下属的一个普通企业,爹不亲娘也不疼,这是地利。如果是上海市属企业,深圳宝安完全没有半点机会。
至于人和,从结果就可以看出,深圳宝安为此做了很多幕后工作,至少和延中相比,不落下风。
天时地利人和,就算推倒再来一次,由于上海、深圳两地的政策灵活度存在相当大的差距,宝安集团赢面依然很大。
不管怎样在线配资查询服务,“宝延风波”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第一次的收购和反收购,其正面效应要远超负面影响。
优速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